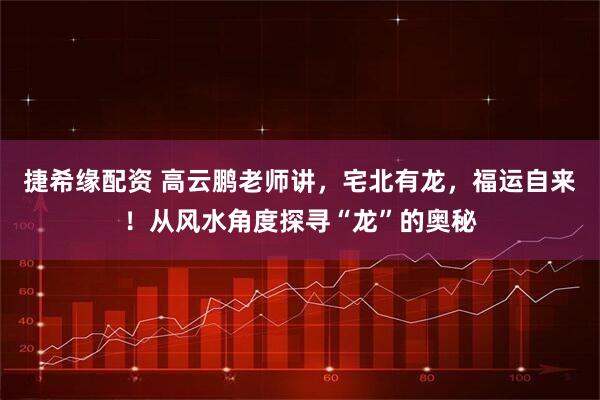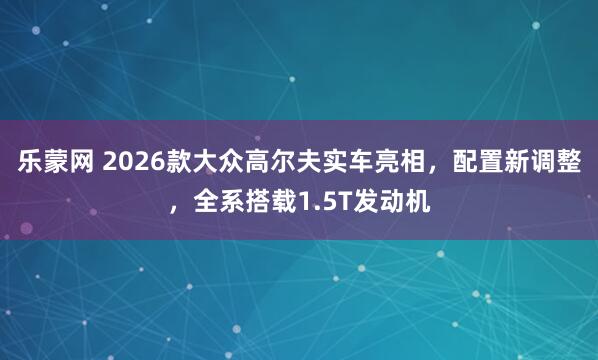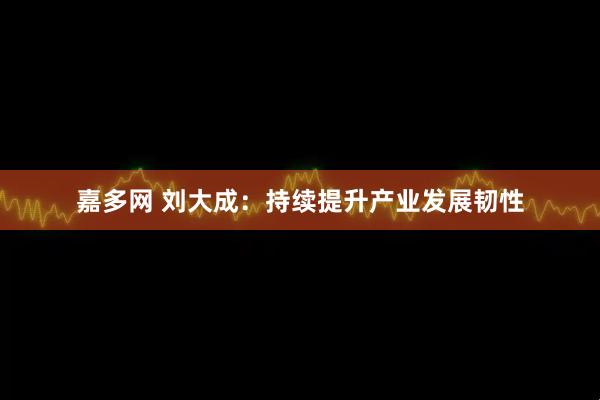
国务院近日召开的做强国内大循环工作推进会指出,结合现阶段我国发展实际,做强国内大循环的重点之一是产业链供应链的自主完备,发挥各地优势加强专业化分工、地区间协作,持续补链强链拓链,增强产业发展韧性。
01
问题的本源
中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5年位居全球首位,且连续3年占全球市场比重超30%。在此背景下,中国遭遇了以美国为首的传统制造强国的强力反制。这一局面的形成,根源在于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全球经济复苏乏力、增长动能不足,以及不同国家及同一国家不同阶层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分配不均等。此外,各国原教旨主义与自由主义、现代主义和世俗主义等思潮因对现实不满而形成的周期性极限拉扯,也加剧了民众对现实的不满,致使民族主义、极端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及(美国)孤立主义不断抬头,“逆全球化”思潮也随之逐步增强。
美国既是“全球化2.0”和“全球化3.0”的最主要推手,也是当下“逆全球化”思潮最重要的发源地。“二战”后期,美国主导推动了联合国、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并确立了布雷顿森林体系,奠定了战后多边合作的基础。此后,马歇尔计划的实施确立了美国在西方阵营的领导地位,北约的成立则形成了美国长期的海外军事存在与集体防御政策,这些举措共同推动了“全球化2.0”的发展。国际标准集装箱的出现,推动全球运输业发生了革命性变革。而1991年华约和苏联的先后解体,使得全球主要国家被纳入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化3.0”体系框架内。
然而,超级全球化并未形成全球法治政府,因此国际市场的法治化也就难以实现,全球公平与公义更是无从谈起。随着工业时代劳动力和资本作为生产要素配置优化的核心禀赋,逐渐向创新与数据作为新的核心禀赋转变,新兴经济体的崛起冲击了原有的经济旧规则。在这一过程中,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产业和不同时段在全球化中呈现出不同的收益和受损。在美元霸权确立和超级全球化形成后,美国中低端制造业产业外移,使得“锈带”地区空心化严重,导致相关行业岗位缺失,2000年至2010年,美国失去了570万制造业岗位,制造业就业人口近十年维持在8%左右,这也引发了利益受损群体的反抗。
疫情和俄乌冲突给美国国防工业体系带来强烈冲击,其关键材料对国外供应链依赖严重,例如,稀土元素进口率高达74%;在国防供应链中嘉多网,35%的电子元器件依赖海外进口。2022年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中39次提到了“韧性”,认为其国防工业的产能和韧性未能达到全面军事需求水平。2025年3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签署的《临时国家防务战略指导意见》将中国定义为“唯一的步调威胁(Pacing Threat)”,并把“中国制造”列为美国国家安全和国防供应链中的遏制对象。
02
对等关税带来的遏制
尽管5月12日中美经贸高层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将美方4月2日、4月8日的加税行政令及中方对应的关税反制措施和非关税反制措施暂停实施90天,但美方仍保留着4月2日之前施加的关税提升、芬太尼20%惩罚性关税、10%的基础加税以及取消800美元中国商品小额关税豁免等措施;中方也相应保留10%的关税反制措施。此外,美国此前对华征收的汽车零部件、建筑与工程Ⅲ、汽车、烟草Ⅲ、电气设备、建材Ⅲ、金属/非金属/采矿、建筑产品Ⅲ、容器与包装、机械、半导体产业与半导体设备、电子设备/仪器/元件、食品、航天航空与国防等GICS三级行业的进口总税率仍超过50%。
美国还限制了“中国制造”转口贸易的通道。要求进口到美国的产品入关时必须提供三张图表证明:一是生产流程图,企业需详细展示生产全过程;二是原料采购凭证,供应链要能溯源到“原料出身证明”;三是能耗数据表,通过真实电力流水账还原工厂真实产能。尤其针对越南、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和墨西哥五国,美国提出免征/征收10%税收的前置条件为100%的通关开箱检查,这导致了通关时间超过抽查时间的3—5倍,一旦产品不符合上述三张图表证明的要求,美国将对所在国征收300%的惩罚性关税,同时对违法企业采取征收10年利润及冻结账户等措施。此外,美国利用美墨加协定,将墨西哥和加拿大的本土零部件占比要求从62.5%提高到75%。受此影响,墨西哥等涉及转口贸易的第三国,对中国部分产品出台了进口加征关税的政策。
对等关税仅仅是遏制中国经济发展的手段之一,美国财政部长斯科特·贝森特针对中国提出,要通过关税和制裁等手段来“平衡中国的不公平贸易行为”。美国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斯蒂芬·米兰则提出,通过重构全球责任分担机制,将安全同盟转为经济同盟(即友岸外包),以关税工具修复“过度自由化”带来的产业空心化。
03
中国持续增长产业发展韧性的路径
在美国贸易政策驱动的“全球化4.0”进程中,“中国制造”的优势不可能长期维系。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必然会着手重建有利于其自身发展的全球贸易新规则,在此背景下,中国需要探索并构建多条提升供应链产业链发展韧性的路径。
第一,积极应对对等关税带来的新挑战,夯实与欧盟“精造”国家、日本、韩国、非洲、俄罗斯等国的进出口贸易关系,提升与中东在“建造”和“智造”领域的合作关系。以德国、法国、意大利等为代表的欧盟“精造”国家以及日本、韩国等东亚“制造类”国家,与中国长期保持互补且协同的合作关系,“中国制造”在该方向的目标是维系这种对等和互补关系;非洲、俄罗斯是与中国有着牢固进出口贸易关系的地区和国家,“中国制造”在此方向的目标是延续以往的成功经验;中东与中国的贸易关系不仅局限于资源互换,也存在着“中国建造”进口对“中国制造”进口的强带动关联,这将成为未来进出口贸易增量的主要目标。
第二,要在未来智慧革命发展进程中享受新红利,利用全球市场的核心竞争优势与他国及他国头部企业进行资源互换,推进全球化新规则下的再次互利。中国未来取得全球化产业协同最大可能的核心优势不一定是稀土的出口互换,而是充沛的电力对新一代智慧革命的支撑。数据、算力和人工智能构成了未来新的生产资料、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埃隆·马斯克认为到2026年,日益增长的人工智能公司将面临“根本性电力短缺”;山姆·奥特曼认为AGI时代将在2030年到来,即“GPT-10”,届时其智商将超过全人类总和,当下其在美国得州建造的“星际之门”超级算力工厂的每个GPU机柜都相当于2000年一个计算中心的100倍,其支撑的核心能力是能源和散热技术。而已经是全球最大电力生产国的中国,还在持续扩张风、光、核、水的发电能力以及特高压输变电能力,未来,充足的电力资源可能是中国参与到全球化竞争的关键支撑。
第三,在已有转口贸易的第三国推动从“中国制造”向“中国钱制造”和“中国人制造”升级。日本在上世纪80年代应对日美贸易摩擦时,一方面,通过与美国签订的“广场协议”使日元升值,另一方面,布局“黑字环流”计划,将贸易盈余以援助或贷款的形式投向国际市场,借此收购全球众多优质资产;同时,日本利用国内面向企业的累进税制,推动民营资本向海外投资。2024年,日本财务省发布的国际收支统计数据显示,其海外投资收益达40万亿日元,顺差盈余(黑字)达29万亿日元,海外净资产超过500万亿日元,且该数据尚未涵盖众多民营资本的私下投资。未来,面对转口贸易受严格限制的东盟和拉丁美洲,中国可借鉴日本的成功经验,推行“中国钱制造”和“中国人制造”。
第四,向内积极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充分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做优做强“中国制造”全球供应链体系。具体来看,将鼓励生产或变相鼓励生产的财税政策,调整为鼓励真实消费的财税政策,以此推动内循环发展。此外,以往及当下出台的拉动消费财税政策,往往针对特定产业甚至特定企业实施消费补贴,本质上仍是变相补贴生产,不仅会支持落后产能和落后产品,还可能滋生政策制定与执行过程中的岗位权力寻租,增加腐败风险。因此,应将消费决策权完全交予消费者,推行分阶段限时但不限品类的定额消费券制度。这一举措既能有效拉动国内消费,又能促使制造业企业在供应链中做优做强,进一步提升其在全球供应链体系中的竞争力。
(作者系中国产业发展研究院常务副院长、研究员嘉多网,清华大学工业工程系博士生导师)
富灯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